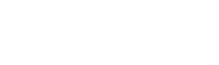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仅有1.04和1.20,均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期的1.8和2.1。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全社会根深蒂固。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不是开玩笑的,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生育率变化(2002-2013)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去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中国港澳台地区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腾讯大家上李华芳的一篇《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显然,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国出生率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东亚要快得多。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别不平等已形成惯例的伊朗,这样的变化也势不可挡:女性开始利用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反对以性别取人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识:在伊朗,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生育2.5个孩子,但不识字的母亲则平均生育6.4个孩子。在中国也一样,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25年出生的中国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岁结婚,生育5.5个孩子;但之后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渐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龄20岁,平均只生育2.7个孩子。简言之,总体上“读书少生娃多”。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现代的文明女性却不再渴望只是成为母亲,“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